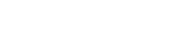两个老年人的爱情战争

天还没亮,水龙头已被拧开,玻璃架上摆满了染发的瓶瓶罐罐。女人抬起堆满泡沫的头,腾出一只筋纹密布的手揩了揩镜子上的雾汽,端详起自己的脸庞。
那是一张的鹅蛋脸,皮肤略有些松弛,却不大看得出年纪。薄薄的嘴唇抿着,或许是因为热,脸颊上氤氲着稚淡的粉色,一双眼角虽鱼尾密布,眸子里却仍脉脉地寓着光。
朦胧的晨光从百叶窗缝隙间渗出来,不多久,大得几乎挤出眼泪的哈欠在门外响起来,裹着衣料摩挲的窸窣,长长的尾音淹没在鸡蛋在煎锅里翻滚的滋啦声中。
尽管听力已经不太好,女人仍在一片此起彼伏的交响中,听到女儿在门外喊:“妈,你真打算和爸就这么分着啊?”
镜中的双眸流光熄灭。女人愤愤收回目光,埋头冲洗鬈发,含混地答:“当然。”
门外的人声高了些:“什么?听不清!”
女人索性将水扭得更大,闭上眼睛,不再理会女儿。
这是第几天了?
大概一两个月了吧。丝丝缕缕的黑色染料顺着水流爬进下水道。
事实上,这是她和男人冷战的第63天。
——这是我外婆外公冷战的第63天。
无声的号角
冲突爆发得一如既往的突然,也发酵得一如既往的激烈。因此这场战役打响的时候,家里根本没人意识到它的严重性。
据我妈神色烦恼的叙述,外公外婆又因为某件鸡毛蒜皮的琐事起了摩擦,而后事态便急剧升温。
“这次的事可挺大的,你外婆先是有句话说冲了,惹了你外公,两人就吵起来,”我妈无奈地叹了口气,“你知道的,一句顶一句的,谁都不让谁,你外公气得要动手——”
她停住,确认外婆不在,便手一抬,脖子一梗,眼睛一瞪, “你外婆就这样儿了——对你外公叫:‘你打啊!你倒是打我啊?你打!’”
我大呼不妙,赶紧问:“然后呢?外公真动手了?”
“嗨哟,你外公哪里经得起激呀?真的要扑过去打——要不是我死死拉着,他说不定真的会打到,就这样已经把你外婆都气得哭了一上午了,已经发了话,这次一定要外公道歉认错,否则拒不归好!唉,这可惨了呀……”
我回了卧室卸下书包,胡思乱想着,一只手在书包里窸窸窣窣地翻找实验数据表,另一只手劈劈啪啪地操作电脑。这次还真是格外棘手,两个人的死穴都被戳到了。屏幕上映出我那研究胞渗的生物论文,只写了一半。未待我手搁上键盘,隔壁外婆的啜泣声就密密层层渗出了墙壁,让我烦恼又怜惜。打我懂事起,外公外婆就是“小闹三六九,大吵年年有”,好不容易近几年两人似有了些“围炉夜话忆青春”的模样,今天的一出吵闹又击碎了夕阳红下的一派岁月静好。两人七十五岁的年纪,四十七年的婚姻,按照我的预期,他们剧本里费劲的吵吵闹闹早就该退场了,该露出赤裸的隽永之骨:那坚不可摧的、相伴相守的爱,谁曾想仍会如此火星四溅、天翻地覆呢?
晚上开饭,外公果然没能得到属于他的那一碗。老人家鼻子一哼,在妻子故作的无视中自己去厨房下面条。在外婆令人窒息的肃冷神色的无声“威胁”下,饭桌上的我们既不敢流露一丝劝和之意,亦不敢说话,更不敢笑。我装作专心地吞着一棵嫩油油的娃娃菜心,我爸和我妈也埋头举箸伸向青色的醉虾——唯一可预知的剧情是,今天的外公无论如何是不会吃也吃不上外婆这道拿手小菜了。
也好,吵闹、赌气、冷战,至少说明他们的感情依然很有活力。
平息罢。
童年的排列组合
和外公外婆住久了,我不免常常幻听到童年的白噪音:
“外公外婆爷爷奶奶,你最喜欢谁呀? ”
突兀的聒噪切断了均匀流动的长河,时间退回至零五年上下。小小的我蹙眉作烦躁状,飞快动动脑子后,老练地给出同一个答案:“外公第零,外婆第一,爷爷第三,奶奶第四!”
外公是我们家人生阅历最丰富、最不摆长辈架子的老人,风趣爽朗,孩子缘极好。我自小喜和外公厮混,并组成默契阵营。外公脸上有几颗老人斑,我和表哥为他取了一个“麻生太郎”的绰号,他大笑且不以为忤。每当他眨巴着眼睛,对外婆“老猪”、“小猪儿”(外婆姓朱)地唤,我就在旁捧腹大笑。然而每当外公吟诗阅报或侃侃纵论古今中外时,他在我眼里又变成博学审思的崇拜对象了。外公初次得知排行时醋意大发,我仍记得五六岁的自己窘得满脸通红,站在茶几旁一只手局促地绕着头发,脑袋嗡嗡作响——想捍卫自己的选择,又不愿意得罪这最好的玩伴和保护神。
排行榜居首的外婆把我自小带大,我和她感情深厚。外婆是主内的典范,生活规律,热爱运动,勤劳干练,除了家务事和电视剧综艺节目,她的脑子里基本不装别的事。她没有老人常有的宛如棉布袋般的无趣与静默,她身材保持得很好,挺拔匀称、充满活力。虽说因常年亲力亲为地操持家务而蹉跎了双手,但其它部位的皮肤却白皙柔滑,爱笑的眼睛、圆圆的翘鼻透着简单、纯真的本性,根部雪白的短发烫染成精神的乌黑山羊卷。人总是清清爽爽,衣服永远大方得体。
在生活上,外公享尽了外婆的照顾服侍,而外婆所看重的,偏偏就是家人的体贴和人前的尊重。“口角诙谐、眼目流利”的外公和她站在一起,总带点反差萌。的确,外公和她一个鬼马精明,一个简单纯朴;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一个永远爱“挑事”,一个永远被“欺负”。年少的我把他们视为一对最标准的欢喜冤家。
在我们这个总体和睦的家里,大家也早就习惯了他们大小摩擦不断的相处模式——每个人都相信鸡飞狗跳的表象下,肯定是我们最喜闻乐见的“情比金坚”。然而随着时间长河缓缓向前流动,儿时无顾虑的野渐渐如跳跃的水波归于平静,这样的摩擦冲突看多了以后,我对外婆的爱——似乎也悄然糅杂了一些怜惜的成分。

脱轨
外公外婆分居了三个礼拜了。
外公回了老家后,忧心忡忡的妈妈跟舅舅通了电话,两边人都几天一个电话打给外公,劝外公认错道歉,讲人情讲事理讲“家和万事兴”,讲外公试图动手的不妥。能讲的都讲了,外公总是一个“休想!”隔着话筒便狠狠甩了所有人一巴掌。
委顿伤心了一段时间后的外婆近日倒是不寻常的容光焕发,山羊卷烫得精致可爱,面颊上抹了乳霜,红扑扑的,烧的菜也愈发好吃。她绝口不提丈夫,但凡稍感劝和之意,便是一句“他不道歉免谈!”扔出来堵住所有人的嘴。调解一度陷入僵局,我愈发觉得气氛剑拔弩张,因此提心吊胆。
我妈没了辙,只得对我耳语:“你看,你外婆这么做给外公看,无非是想让他早点灰溜溜地回来认错,”她眼珠一转,捅了捅我:“你小,面子大,你去劝,聪明点,把你外婆哄高兴了不就皆大欢喜了。”
我只得佯装叹息一声,小心翼翼道:“外公缺了你照顾,一个人在老家肯定活得很差。”
“他活该。”外婆面无表情。
“都三周了,外公罪也受啦,反省也反省过啦,现在肯定愧疚得不行,不过面子上有点过不去啦。要不然外婆……你给他个台阶下?”
外婆目不斜视,轻启双唇,不轻不重地扔下两个字:“离婚。”和从前她无视我们玩笑的模样如出一辙。
离婚
我撇着嘴,手握淋蓬头,机械地冲洗身体。根本不可能。七十五岁对于大部分人而言,无非是个和老伴闹闹小矛盾,在家享受子孙绕膝天伦之乐的年纪。两个老人离婚,未免也太荒诞了。现实一点罢,一辈子都过来了,要离婚——早就离了,一点小摩擦怎么可能如此致命?就算执意分开,难道就此孤独终老?还是换个新老伴儿,来一场轰轰烈烈的黄昏恋?
浴室里水汽氤氲,外面的纷扰一下子退潮至遥远的海床外。省省吧。吵架归吵架,日子还是要过。
他们的爱情,应该是一家相聚时津津乐道的故事,他们的纷争也差不多该载入史册,成为我们偶尔的回忆。他们应该像所有其他同龄人一样,一辈子打打闹闹又相濡以沫。就像豆瓣微博朋友圈里其他人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一样,并肩在田野里城市里走路,被后面的小辈悄悄拍下,配字“看见了爱情的模样”,再加颗爱心——行云流水的操作,完成,po出。
或许我该记录一下两人分居的模样,再配它个“朋克夕阳红”?
洗发水顺着掣动的嘴角流到嘴边,苦哈哈得辣嘴。我笑了一下便笑不出来了,突然莫名地觉得烦。
外公外婆分居的第六周,我开始不确定这场看似可短暂消弭的战役究竟何时结束,或以什么样的方式告终。我也开始怀疑劝和究竟是否有必要,以及它究竟正确与否。事态一天天恶化,两位老人好似都死了心,面对爸妈舅舅们的劝和,二老连句对对方的抱怨或指责也没有了,淡然得好似离婚真的已成事实。
夜晚独自躺在床上,仰面瞪着黑暗,记忆的幻灯一张一张切过。我幼时看他们吵架,大人们劝,我和表哥却像看喜剧一样兴致勃勃,我或他会用水彩笔在纸片上歪歪扭扭地写:相声演出售票,一万元一张。回头一看, 来时的路上这样的入场券漫天飞翔,五彩缤纷,热热闹闹。我瞪大眼睛仔细瞧,它们却约好了似的都来迷我的眼,纷繁缭乱,让人看不清所有事故的原委,只有个模模糊糊的影子——话不投机便开始哄吵的一出出闹剧,从笑着互掐到哭着喊着闹离婚都有。
平日里出了什么小岔子——盘子洗得慢、快递忘了寄、下雨天遛狗忘了关门、我喝光了你茶杯里的水而忘了给你留一口、没把对方的牙刷归置好——似乎都可以被引燃。
两个人你一言我一语,不出三句必定脸红脖子粗:
“你这人就是太霸道要强!凡事只想到别人的错!从来不反省自己!”
“你这人就是吃粮不管事,自私自利,对人从不体贴!”
外公不像爷爷,对脾气不好的奶奶充满包容和体贴,他也不像我爸,得罪妈妈时虽口不认错却知道买花送礼物讨妈妈欢心;外婆也不像奶奶,对爷爷是刀子嘴豆腐心,照顾体贴得细心,她也不像我妈,和爸爸闹不愉快后总能理性沟通。或许如此使然,他们从来都不是平和的。然而纵使我对外婆的一丝怜惜从童年一直长至今,又能说外婆无辜么?似乎也不妥,一个巴掌怎么拍得响,他们好似都是不肯相让毫厘的人。
孰对孰错、责任在谁从来都是剪不断理还乱的一团乱麻,早就和那些发黄的旧照片一起,被岁月晕开,模糊了。
青春年华
“他们在最好的青春年华相遇,在最蹉跎的岁月走进婚姻。”家里人讲故事时都喜欢这么说。
1943年,他出生在水土丰饶的江苏泰县。父亲管理着自家庞大的作坊,母亲是大地主能干的长女,家境殷实。然而随着1951年,父亲被划定了成分,紧接着1953年公私合营,他也初尝世道变迁的辛酸,从任性调皮的小少爷变成了发奋读书的优等生。文革前夕,他又因被人匿名重提历史帽子,高考梦粉碎。尔后父母被抄家游斗,他下乡插队,学农学工,到1971年家里平反时,他已经成了农场农具厂的合同工车工。
也是那一年,她嫁给了一无所有的他。
她是一个小商人家庭的老幺,家风本分。她13岁时母亲就病故了,从小便没有一点娇惯和痴嗔。老照片上的她肤白大眼,两条大辫子,清爽干净的素色布衣,气质出众。她和他还恰好分别是校女篮队和男篮队的队长。这样两个郎才女貌的同龄年轻人,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彼此的初恋。他插队的那十年,风华正茂的她拒绝了所有仰慕者的追求,毅然出嫁。没有拍结婚照,没有摆酒席,所有的嫁妆只是几件新衣,他家能拿得出来的唯一的礼物是一块上海牌手表。
成婚后的他们起初聚少离多,但两个人相爱,不觉得日子辛苦。他逐渐建立了自己的事业,工作忙,家务事几乎从不沾手,“油瓶儿倒了都不扶”。他对她的爱主要体现在上交工资、经常给她买衣服、带她旅游。他喜欢社交,经常把同事带到家里来小聚,她就得忙里忙外;他喜欢学习,关注时政要闻、经济商业,她却天生对这些没有兴趣;他重视投资理财,敢于冒险,她永远只选择存银行——漫长的婚姻生活中,渐渐生出了杂音。两人的口角纷争常因“不干家务”、“对人不体贴”而起,又都是直性子要面子的人,言语上不肯服输的,结果自是周而复始的激烈较量。
在锅碗瓢盆间的争执中,他们的头发终于渐渐白了,退到了全家福的后排。他总还想做点什么事——他的强势不允许自己的存在感渐渐消去。而这些在她眼里都成了自私的借口。
大家都笑笑:二老的身体还是真的太好,还有精力吵吵闹闹。小孩子一样。
他们总是让我茫然。一轮又一轮的春秋,他们都成了祖父辈的人,我总觉得他们确乎爱着彼此,却没磨出个所以然来。致命一般地,两人还未学会相处,便已老了。
自始至终,一切都不是我们想的那样。
我搜寻着记忆。有那么一两次,两个人都很严肃,郑重地对大家宣布:“我们实在不会沟通,过得累。” 一家大小都笑嘻嘻的:“走,带你们去看场戏!最近王佩瑜那个《春水渡》特别好!小百花越剧团也来天蟾逸夫舞台表演了,我们定得早买到了好位子呀。” 又有那么一两次,两个人闹得凶猛,然而我更凶猛,举着塑料话筒激情模仿“甲方乙方”、“新老娘舅”,一张嘴皮子伶俐翻飞,爸妈舅舅舅妈在旁边笑着劝架。
多少濒临破裂的临界,都如此让我们这群说三道四的人给强拉了回来。一家的朱口白牙,都张着嘴哈哈地笑,笑得唾沫横飞,唯独他们俩沉默着,闷声不语。粉红色滤镜安插在镜头前已久,几乎长在了相机上,他们的表情我从未看得分明。
待我再去看卧室里钢琴上的全家福,每个人的脸庞似乎都带些陌生的微妙。那些和煦微笑的、朱口白牙的脸,有的或许依然相信他们情比金坚,有的或许在装聋作哑以保他们安度晚年,也有的或许和我一般傻,许久都未看出端倪,认定他们不过就是一对欢喜冤家、我们的快乐源泉。

愈合
年末,外公外婆终究还是和好了。外公最后被大家逼着道了个歉,搬了回来,这事就算了了。这场三个月的大战无疾而终,一如往常,并在这一刻起被载入史册,正式翻篇。然而我总觉得,外公外婆各自的一部分也在时间里被弄丢了。从此又是一声声的“老猪”,生活像在外溜达了一圈,又回到熟悉的轨道。
皆大欢喜。
圣诞节,外公突然宣布他有个六十年未见的朋友从加拿大回到上海。那是一个女同学,也姓朱,当年他曾是她的初恋。我拿眼角悄悄瞄外婆,她风淡云轻的,大开着洗手间的门在染头发。我们商量了一番,于是张罗一顿饭。
老太太戴着眼镜,略有些胖。一见面,外公外婆和客人都惊呼认不出了,一番说笑后遂天南地北地聊,整顿饭吃得亲和而平淡。爸妈坐在一旁,也舒了嘴角笑着。温暖的灯光中他们三人像老友般长谈,玫瑰花瓣兀自恬静地躺在铺着白布的餐桌上。
待到分别时,站在平安夜徐家汇的晃亮霓虹中,也姓朱的老太太一只脚跨进出租车,挥手道:“再会了!下一次见不知何年何月,今天见到你们真的很开心!”
十二月的风用老人的声音呼喊着,在车水马龙上奔跑着。
“再会了!”
我坐进开足暖气的车里,“嘭”地一声用力关上车门,冷风被关在外面,卷着微雨呼啸了一阵便走了。我坐到后排外公外婆中间。或许是因为冷,外婆的脸色似乎更白。外公把手放进袖管。车厢里静默着,两人各自托着腮看窗外那飞逝的绚丽的梧桐树——它们光秃秃的,却挂满彩灯。风一来,那些连在一起的硕大的灯球就扑簌簌地抖起来,似乎下一秒就要从树上坠落。然而风终究刮到别处去了。

健康快乐每一天个人博客版权声明:以上内容作者已申请原创保护,未经允许不得转载,侵权必究!授权事宜、对本内容有异议或投诉,敬请联系网站管理员,我们将尽快回复您,谢谢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