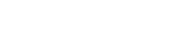老年人无处安放的性与爱,垂暮之年,许多老人依然有着性的欲望

本文节选自网文作者:全民故事计划,有删减,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图片源自网络侵删
声明:本文为小说,内容都属虚构,包括地名、职业、机构等等,皆是文学创作,请勿对号入座。
这是一个鲜少被提及的话题。垂暮之年,许多老年人依然有着性的欲望与爱的能力。
性社会学家潘绥铭在《给“全性” 留下历史证据》中提到,在中国,55-61岁的老年人中,53%的人每月有一次性生活,39%的老年人可以达到每月3 次。而性学家金赛的研究则指出,94% 的男性和 84% 的女性过了60岁仍有性行为。
当我们拨开迷雾,一步步踏进老年人的情爱江湖,便如同走进了一座婚姻围城。面对不再年轻的身体和疲惫的婚姻,里边的人困苦挣扎;背负着复杂的关系与沉重的压力,外头的人小心遥望。他们有着不同的身份,却同样煎熬着,追逐过,或也曾迷失在这条性与爱的路上。
《老年人无处安放的性与爱》上期回顾:老年人无处安放的性与爱:被无视的性谜题
一
挣扎崎途——婚事欲说还休
垂暮之年已至,但他们仍存着如年轻时对于陪伴、对于爱情的向往,而在追求性与爱的路上,山高路且长,他们要跨越的还有很多很多:老伴去世后,胡天曾经遇到过一个电影演员,他可是真喜欢,60岁了“比范冰冰章子怡长得还要好看”,追了一年多才追到手。
但女儿一句话就给他打了回去,户口本、房产证都给他收着,这婚就是不让结。女友在胡天面前哭得梨花带雨,但他也只背过身去,“算了算了。”
47年出生的睢阳在莲花山相亲角给自己挂征婚信息,自称“阳光老太”,一挂就是7年。路过的行人如织,闲言碎语不绝于耳,“都这么大年纪了还找对象呢……”外部极大的舆论压力、子女强烈的婚姻控制,种种的这些条条框框织成一张网,笼罩着他们,束缚着他们。
人言可畏:六十耳难顺

现在的胡天,在兄弟姐妹眼里就是一个“败类”、“坏蛋”。
3年前,胡天正满60,老伴去世,这是胡天日日寸步不离照顾她的第7年。在妻子离世的7天后,胡天领着新女友回了家门,两人过起了同居生活。
北京有规矩,老婆走了以后,一般要守三年。嫂子看不过去了,训他,“本来挺敬佩你的,媳妇照顾这么多年挺辛苦的,好家伙,几天就找一个。”
胡天家姐弟七个,他最小。同在北京,他每年只跟自己亲兄姊聚一回。
妻子过世后,胡天女朋友不断,哥哥姐姐们都看不过去,“他们就觉得你这个就是不正经,不是好人。”胡天扯了扯嘴角,这话他可不爱听,“这每个人的私事谁管得着啊。”
胡天心里话,你饱汉子不知饿汉饥。
在这七年里,用胡天的话说,自己是“长在医院里了”。
那会儿,为了给老伴挂上院长的号,胡天经常是排队就排上一宿。院长的号 500块一个,很不好挂,医院一个礼拜就只放一个号。排队的地方有一排报纸,等放号的时候,排队的人来了20好几,可号就这么一个,一堆人就打起来了。“我今儿就奔什么,打一个够本,打两个赚一个,跟我玩命了。你就来吧,爱多少多少人,我就跟你们干了。谁不难?”
号最终给胡天挂上了,医生对胡天和他老伴来了这么一句,“对不起,治不了。”胡天的心一下沉了。春天夜晚八点的菖蒲河体感温度不足10度, 胡天只着单衣,手里夹着的烟头闪着红色的火星忽明忽暗,“那医院还有一名字叫‘人生最后一站’,一进就倒计时,没几天活头。可不去也不行啊, 挺难的。”
眼看着老伴就要撑不下去了,胡天凑到她跟前说,“你到那,你等着,那里有谁欺负你,你先忍着,等我去了再找他们算账,你知道我的。”老伴最终死在了胡天怀里,临走睁着眼,侄子帮他把老伴的眼睛合上了。
“孤独比贫穷更可怕。”老伴走了,胡天回家一个人对着 90 多平的大屋子,空荡荡的。说话的人没有,电视一宿一宿地开着,灯也亮着。胡天爱窝在客厅的沙发睡觉,时常四五点醒了,电视里节目依旧不知疲倦地演着。
“倒不是害怕。”胡天胆子尤其大,年轻时曾经赶过马车,在枪决场里,枪毙执行后的犯人他一个人装车拉到火葬场。
胡天眼皮耷拉,本就细的眼睛眯成了一条缝,谈到性,他也说得坦然,“就这样我能幸福吗?这是我总结出来的至理名言,没有性哪有幸福,确实是这样的。”
同样是2016年,64岁的王予登上了《选择》的舞台,这是北京卫视的一档婚恋交友类节目。在菖蒲河,《选择》可是一档明星节目,几乎遇着的每个老头老太太都跟我们推荐过。
几个星期以前,王予在电视上看见了一位来自内蒙古51岁的女嘉宾,一期节目过后,他心动了。王予边跟我们说,手一直在捋路边的叶子,枯叶在他手里一揉就碎,“我这人有点颜值控。”他低头不好意思地笑了。
去之前,王予跟女儿提了一嘴,女儿没同意,说让亲戚看见了多不好意思, 让王予别上了。可王予还是没忍住,瞒着孩子就报了名。
为了显得与众不同, 王予准备了一片面膜,编导在上台前对他说,“你这够呛的。”可最终他还是把面膜贴着,背对着观众登了场。
同场竞争的另一名男嘉宾的姐姐为自己的弟弟“加分”来了,主持人问王予,“你有亲友团吗?”猛地他唇角紧闭,眼珠左右晃了晃,身板挺得笔直, “我只能自己给自己加分,我存折都拿来了。”他忙说。
王予从裤子口袋里拿出了存折和一个首饰盒,那里面存着他这几年的退休工资和一枚特地跑去菜百首饰买的黄金戒指。
那时候,王予已经领过三次结婚证了,可表白的时候,他的手还是像一个毛头小子一样紧张得直哆嗦,“您好,我就是冲着你来的,可以说是一见钟情⋯⋯”
王予的黄金戒指最终没被接过去,女儿那边的电话却来了。
原配的亲戚也看到了他的节目,说他丢人,年纪这么大了还上台相亲, 让人看见了面子挂不住。电话的这头,王予沉默了。

在北京菖蒲河公园受访的王予 | 供图唐梓聪
我们曾在深圳的街头进行过一次针对15-60岁范围人群的随机问卷调查, 在对老年人的印象调查问题上,357份有效问卷中,“清心寡欲”的选择量达到143人次,仅次于“健康”一词。在不少人的理解中,已然脱离生殖年龄区间的老年人,早已与“性”无缘。
我们发现,在性话题上,相比于其他年龄段的人群,老年人往往需要背负更为严苛的社会期待。在性社会学家黄盈盈看来,这就是所谓的年龄政治的一种。
同时,彭晓辉也指出,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性禁锢文化的一种延伸,“在我们的传统中,为了生殖目的的性才是合乎规范的,而为了满足愉悦的性则会被当作淫欲。这实际上是一种无知。”
婚不由己:反哺的管控
“都这把年纪了”成了多数受访老人不愿登记结婚的说辞。而程南则嫌麻烦,认为双方都有孩子,怕“搅得两家不太平”。
他享受这种不适合就分开的自由,当然,为了表示自己的诚意,程南给现在的老伴买了套房,前提是“不登记”。
程南的儿女们对这件事没有异议,他自己喜欢就行。
70出头的温如君在两个女儿找对象时也秉持孩子自己喜欢就行的原则。可他怎么也没想到,几十年后,反倒是女儿要管着自己了。
2006年,和温如君相伴41年的前妻因肺癌去世。前妻走了以后,一次在回河源老家的车上,温如君遇见了他的现任妻子,两人互生好感。温如君满心欢喜回家跟女儿说起这件事,女儿们都不支持,反对最强烈的是他最疼的小女儿。
2008年1月,温如君不顾女儿的反对,再婚了。
小女儿结婚的时候光是金手镯他就给买了两个,后来在深圳东门那边买了一套房子,也直接送给了小女儿。但疼归疼,“我要办的事,我有我的自由,法律没有规定就不准结婚了。”
结婚后不久,温如君提出希望能跟现任妻子住到之前给小女儿买的房子里去,小女儿不同意,怕这个后妈争财产,二话不说背着他就把房子低价卖了,能值 300万的房子当时不够100万就出了手。
至今十年有余,温如君再没有收到过小女儿的电话,也没有听她再喊过一声“爸爸”,他们几乎断绝了来往。
“太糟心了,我最疼她,她就这么对我。”
讲到再婚,他回忆起跟前妻谈论过这个生离死别的话题,前妻跟他说,我要是走了,你就再找一个吧。
他喜欢柔柔顺顺黑色的长发,可偏偏前妻是个打篮球的运动员,留着一头清爽的短发。“她不是那种很漂亮的,但我最喜欢的还是她。”
温如君掏出了自己的钱包,夹层里是一张他年轻时拍的证件照,油头锃亮, 西装笔挺,他轻轻抚去了夹层的气泡,“我年轻的时候帅吧。”语气自豪。
“人啊,都是有感情的动物,老人有老人的感情,年轻人有年轻人的感情,你让他这么孤孤单单的,他会发神经的。”
那时候温如君没有想到过事情会是这个局面,“现在很多老年人想再婚的,大多都是子女不同意。他们自己有家,当然没想到爸爸一个人是怎么过日子的, 再多钱给我也没用了,你给我再多钱我也不要!”
半个月后就是春节,今年大女儿邀请温如君到自己家过年,但他想了想,拒绝了,还是打算像前几年一样,陪妻子到东莞的继子家去,“在那里过年能过得舒服一些。”
相比于温如君,睢阳的爱情总是在儿女的“掺和”下戛然而止。
今年72岁的她,从2012年起在莲花山相亲角给自己挂征婚信息,每周日更换一次,7年风雨不改。这么些年,看到她的信息之后打来的电话数也数不清,她已经忘了自己失望过多少回了。

睢阳贴在莲花山相亲角的征婚信息 | 供图李可程
4年前,睢阳遇见了一个比自己大3岁的人,出生于高知家庭,性格沉稳,这是睢阳这几年来“唯一一个惦记着,愿意跟他走的人”。没事的时候睢阳就总爱约他在他家附近河边走走聊聊,“话聊的没个正经,但就是说也说不完。”
好景不长,睢阳的出现让男人的女儿感到不适,女儿当即买了一张机票,把在这里待了20多年的爸爸送回了黑龙江养老。
钱都在女儿手里,男人没有办法,他妥协了,决心回家等老房子的拆迁款,给自己找条后路。离开前,男人给睢阳留下一句话,“你该找就找,到了那天你还没找到, 要是你不嫌弃我,咱俩还走。”
虽然心里还有期待,但睢阳直觉自己耗不起了。1年多以前,她又遇到了一个大自己9岁的男人,“我差点都要嫁过去了。”
他们协商好开始3个月的试婚,最后如果双方都觉得可以的话就去登记。
3个月里,他们为结婚翻新房子,光是换木地板就花了几万块钱。男人八十大寿,睢阳以女主人的身份上了席,第二天,她就决定把自己的衣服细软、碗碟杂物打包,天天这么来回拉,早上满车来,晚上空车回去, 睢阳心里高兴极了。
可就在男人和儿子的一次见面之后,睢阳发现男人有些不对劲,她问是怎么了,男人支支吾吾,最终还是说出了口,“儿子说了,不登记。” 这个疯狂的老太太甚至愿意两人登记后马上离婚,就是为了看到男人的态度。可男人没说话,她的幻想破灭了。
睢阳看透了这个事,“不是说因为你不登记,而是说现在你就受儿女左右,那我就永远只能活在这个阴影中间。”
没多说什么,一个电话,她让快递给她捎了个大旅行袋,默默地把自己之前一车一车拉来的东西,又一件一件地收拾了起来。
除去对新增家庭成员自然的心理排斥,彭晓辉指出,因为“性生活的背后可能就是财产的消耗问题”,故子女在父母再婚问题上表现出的高介入度,极大程度上是因为这段婚姻将会涉及到其切身利益。
虽然中国向来推崇“孝文化”,但这更偏向于针对解决父母衣食住行等生存方面的需求, 却往往忽略老一辈人正当的性生理与心理需求。
睢阳从男人的家离开了,带走了自己所有的痕迹,告别了那段尚未珍重便已夭折的婚姻。
非富勿扰——被定价的婚约
深圳最大的相亲角,坐落在深圳市市中心的最北端的莲花山公园。
棕榈树下,方圆不足200平方米的小角落,两面架子上密密麻麻地挂满了数百张征婚信息。差别迥异的人们被齐刷刷地“压缩”成了一张张A4纸,浓缩为一排排的方块字。
在相亲角的东侧中部,那里有为老年人专门开辟的一方天地。与年轻人无异,除去身高、年龄、性格等基本信息, 经济条件亦为老年人择偶时看重的关键指标。“经济好, 住房好”、“有退休金”、“有一定经济基础”⋯⋯这样的要求在择偶条件中不难被发现。

张贴在莲花山公园相亲角的征婚信息 | 供图李可程
在2000公里以外的北京菖蒲河公园,除去物质基础,可享受更为优厚的养老和医疗标准的北京户口则更是“香饽饽”。
对于老年人来说,早已过了退休年龄的他们,想要在北京或是深圳安定下来,有一席容身之处,则成了他们最大的诉求。相比于女性,更多时候,这等“硬性规定”则会落到老年男性的头上。
于是,一套独立住房,成为了横亘于这些单身老人与重组家庭之间一堵难以翻越的高墙。

在菖蒲河公园携手跳舞的单身老人们 | 供图唐梓聪
年后再见熊大爷时,他的脸上有藏不住的喜悦。“我二女儿在惠州有间空房,她让我过去住。”
熊大爷50岁时搁置了家乡的棉花田,来到深圳后,就一直住在大女儿家,和女儿一家也和睦至今,有独立的房间,还有孙儿陪伴,生活便利热闹,没什么让人不满意的。能让熊大爷如此高兴的,不是那间空房,而是空房背后重拾生活的机会。
20年前妻子肿瘤去世,熊大爷的全部财产只剩下乡村80平米的瓦房,还有2亩多的田地。农村的生活靠自给自足, 棉花田一年仅能给熊大爷带来3000块的收益,这样的条件,这样的年纪,不管在哪儿,只能安分地守着自己的日子。
熊大爷坦言,不是没动过再婚的念头,那时才45岁,还会有性的冲动,“要是不会感应,那生命就完了”。
妻子离世后不久,在亲戚的介绍下,熊大爷开始和一个女人同居在老屋,这段关系持续了四五年,以女人的落跑结束。熊大爷能给的,只是解决温饱和住处问题,而女人喜欢赌博,熊大爷没有足够的积蓄任她挥霍。熊大爷曾提出和她一起去深圳谋份工作,改善生活,但女人拒绝了。在熊大爷看来,“她不够听话”。
在深圳,熊大爷也遇到过一些看对眼的人,但情况没有丝毫偏差,“没有钱, 只能做朋友。”事情总被拦腰截断。
当提及家庭条件时,话题再也无法深入下去。
房子是熊大爷绕不过的坎儿。他从不和儿女提起再婚的事儿,他明白,自己寄居在他人屋檐下,15平的空间再容不下一位陌生女人。熊大爷渐渐接受了现实,“没有经济基础,谈感情也是空想”。
年纪大了,“无所谓”成了众多老人的口头禅。熊大爷有时想想觉得, 一个人也挺好,游戏人间也是一种选择。
在深多年,接触的人多了,他在公园的布景里活得游刃有余,熊大爷深谙公园的游戏规则,碰上聊得来且有同样需求的单身女性,性话题从来都不是禁忌。
大家心里都明白,上这儿来谈婚论嫁太难,纯粹的性关系兴许来得更实际。

在北京菖蒲河公园相亲的老人 | 唐梓聪
6年前,熊大爷遇上了一个西安女人,她待熊大爷很好,还给他报了个旅游团同游北京,熊大爷现在想来还很激动,“那是我第一次出去玩,我从来没旅游过。”
熊大爷曾以朋友身份将她带回女儿家吃饭,可见家人没有其他意思,便作罢。
熊大爷又燃起了结婚的欲望,是考虑到了之后生活的诸多不便。女儿有自己的家庭,“始终是外人”,他需要一个比他年轻的女性,照料晚年生活。突如其来的空房犹如一剂强心针,他开始规划起新的生活。
但短暂的喜悦后,熊大爷又陷入了某种不确定。他没有退休工资,从前在农村的唯一出路就是劳作,一年前荒废许久的田地被政府强制性收走,一亩地一次性补贴1万多块,“两亩多田,4万块,在深圳这个地方,管我一辈子够吗?”
而我们在菖蒲河公园遇到的王予,北京户口,有房。但现在他依旧要为如何挽回他“错失的”的心上人而费着脑筋。
为了给孩子省点钱,3年前女儿提出要给自己买套房时,王予选了现在的住所。他住在门头沟的王平镇,那是一个需要在北京1号线坐到起始站苹果园, 然后坐32站公共汽车才能去到的“山沟沟”。
在菖蒲河前后七八年,王予遇到过不少的人,但事情总成不了。“女士们一听到我住在这旮沓角落,就都跑喽。”
3月中旬,就在我们离开北京不久,王予给我们发来了微信,他告诉我们,9号他又在菖蒲河遇到了一位女士,无论是形象、身材、言谈举止都很符合自己的想象,他说,这就是他“心目中的女神”。
刚认识一礼拜,王予迫不及待地要讨好心上人。他在网上给这位女士买了两件旗袍和一件白色的毛衣,女士却说不喜欢,让他赶紧退了。但这段小插曲并不妨碍他大段大段地憧憬着两个人的未来。
“你想看她的照片吗?”一天晚上,王予给我们发来一段语音。倏地下一条信息跳出,他显得很高兴,“现在不让看,以后等照了结婚照再给你看吧!”
“可能是菩萨给我安排的,这回我不能再错过了,我要跟她一心一意过好下辈子。”王予发来语音,语气肯定而温柔,“我们 9 号认识的,九可是个好数字,我们的生活长长久久嘛。”
而就在他们认识的第9天,分手来得猝不及防。
事情就发生在女士从王予家拜访回去的第二天,他怎么也想不通,“为什么翻脸比翻书还快呢?”
王予的电话被拉进了黑名单,但他不死心,每天还是小心翼翼地用微信不时问候着。他觉得这也许还不够,在被提分手的当天,他专门坐了1个小时的车,来到镇上的手机营业厅,给“狠心的”心上人的号码充了200块钱话费。
王予打算每月如此,直到她回心转意为止。

王予的背影 | 供图李可程
因为物质条件缺乏竞争力,而导致的那些没有结局的悲伤故事,几乎每天都在上演。以房子为代表的经济条件,属于生活资料的一种。彭晓辉指出,生活资料的占有量往往与性资源呈现此消彼消、此涨彼涨的正相关关系。
“婚姻不同于爱,爱的目的是给予,而婚姻的目的是获得,是索取。”如何在给予与获取中寻找其中的平衡点,这也许是老年婚姻亟需思考的关键问题。
二
在性的边缘试探
在我们深入了解这些老人的性生活时,发现了事情的不对劲,与我们对话的37名60岁以上的老年男性中,15人明确表明自己正在与性工作者有着某些接触,超过三分之一的占比在我们看来有些不可思议。
这些男性的年龄在70岁上下徘徊,甚至有三位80岁高龄的老人。除去因处于无伴侣状态而发生的性交易行为,婚外性行为在老年婚姻中也绝非罕见。上述15位在嫖娼中试错的老年受访者中,有8位目前仍处于再婚状态。
隐蔽的性图景
在获取老何的信任后,他承认自己也触碰了婚外性行为的黄线。事后他告诉我,他原本不敢说的,担心自己的形象落于“下流”,遭人鄙夷。
吐露如此私密的话题让他有些不自在。在公园的湖边,他支支吾吾,言辞闪烁,沿岸路人不断,几次话到嘴边,又被他吞了下去。在沉默间隙,他摘下了墨镜,仰斜的头正对上正午的太阳,感有眼疾的双眼被强光刺痛,眯成一条缝,他猛地将头收回来,眼神对向了我,又立刻下意识地重新戴上墨镜。
“我想这个跟道德没关系, 你应该正确地认识这个问题。”他想尽快结束这个话题。
在他们的描述中,故事通常是在“发廊”发生的。这些“发廊”分布在深圳各大城中村错综复杂的昏暗巷道里,或大或小,由单人经营,或者稍大点的,透过推拉玻璃门可以看到四五个女子的身影。
在城中村的入口 处,向街口闲散的板工稍加打听,便能准确得知一些性交易的场所,板工提醒,这些地方大多晚上才会“开门 营业”。
白天,各处巷道口站守着一位治安管理人员,交叉着巡逻街道,天黑了便会撤去。要在白天行方便通过熟人引荐,可以去寻找位于握手楼2或3层的一些“个体户”。
老何所在的小区紧邻着一座城中村,他常光顾一家规模较大的“洗头房”,外部设施齐全,“能洗头,能洗脚,能按摩”,往屋子深处走,后面的空间被隔成四五个小室,隔间不大,除了一张床,没有多余的家具,墙上零星地粘贴着大大小小的裸体像,让人知会小室的功能。
房间被收拾得很干净,“如果环境不好的话,这一次去了,下次再不去。这里舒服,夏天还有空调开。”干净的空间使他安心,减少了染上疾病的疑虑。老何通常会待上1个小时,拉上窗帘,便开始计时。在纯粹的消费维度下,性只局限于生理的行为,逃离了柴米油盐、资产分配,老何感到了“单纯的幸福”。
陈香港对这事儿也看得轻松,他不常去,中间间隔两三个月,按摩店会有不一样的面孔出现。
在按摩的间隙,陈香港习惯性地和她们聊天,再决定有没有心思继续下一步,“有时候有的女孩子未免合你心意的嘛,看聊不聊得来。就像你吃饭搭桌,不合适都要走人啦。”遇到模样标致的,“你都想坐久一点,看多几眼啦”。
城中村里的性交易风险高,但价格相对便宜,200元一次是业内均价,几十元的交易也能达成。对一些经济不太宽裕的老人来说,性生活方面的支出相应减少,在性的质量和安全度 上也就做出了让步。
农民出身的熊大爷没有固定的养老保障, 每个月匀出百来元作为性消费是他能承担的最大限额,超过 一百元一次的性交易在他看来是“不合算”的。
以前在湖北县城做建材生意的时候,老何就没少出入这些娱乐场所,“我在老家就知道,有些发廊、洗脚屋是什么地方”,来了深圳后,老何知道顺藤摸瓜的道理。
除此之外,在公园的社交圈内也能获得足够的性资讯,隐晦的性行为和性资源在这里被毫无顾忌地相互交流,分享。老何告诉我们,“有些老头 的老婆有病,或者去世了,去那种地方就多了。”
最近两年老何想通了很多,出手越发大方,“钱再多,又带不到棺材里面去,多了没用。我也留不了什么给子女。”老肖现在已经很少去城中村了。老何求教于“有经验”的朋友, 打听了一些更私密的女性性工作者。老何有她们的联系方式, 打个电话,约个地点,素未谋面的密会让他面红心跳。

地点很少选在酒店,“一是怕不卫生,二是公安局查得严”,尤其是一些私人的小旅馆,是扫黄打非的重点对象,老何也怕噩运落到自己头上。他要求在对方家中见面,没有比家更安全的地方。
但对于另外一小部分老人来说,手机成了更隐蔽的所在。线下的关系延续到线上的新图景不止于此。有人忙着满足自己的性需求,寻找出口;有人却忙着将性资本打包寻租,成为出口。
赵一的QQ名显示的是“深圳夕阳盛世”,点击进入他的个人空间,不同寻常的内容让他的身份明朗起来。赵一今年69岁,通过个人账号经营着一个隐秘的线上性会所,他在其中充当掮客,不断发布男性性工作者的信息,操作交易。
这些男性分布在深圳、广州和东莞,年龄均在50 岁以上,以60多岁的男性居多,甚至包括一位80多岁的老汉。
赵一的交易开始于2014年的4月,至今手里已经掌握着178个老头的资源。178号是4月3日新到老头的编号,信息被置顶在赵一的空间相册里,配文醒目:“新人刚出道,欢迎提前预约”。
他喜欢以号码标识他们的身份,再配上“儒雅帅老”、“清瘦帅老”的“品类”介绍,加上一张风景肖像图便可“上架出售”,将消息发布到个人空间,最高的浏览量可达2000。
赵一曾建立过会所的网页,但涉及非法内容很快便被查封。QQ 上单一的信息传播方式大大限制了他的成交量,只能耐心地“等鱼上钩”,他不甘心,重新设立了新的网址,但不出意外,新页面没过多久就再也打不开了。
平均每隔一个月,赵一的会所会增加一位新成员。为了拉拢生意,除了在个人空间投放新消息,他会第一时间私发给所有联系人。
和赵一做交易很简单,不用签署任何说明,交易明码标价,“过夜晚700,外加来回车费;快餐2个小时,服务一次500 元”, 私信赵一预约付款,即可获得对方的联系方式。
性原是本能,道德枷锁却无处不在,当人性与道德碰撞, 他们也只能在无处安放的性中浮沉挣扎。
性错推手
他们不是不知道,一旦这么做,面临的可能是染病和法律制裁的巨大风险。
然而,幸福的家庭总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却各有不同。无法通过婚姻得到情感和性的诉求,这15个老人甚至是他们身后的大多数,总有不得已而为之的理由。
其中伴侣的高丧失率便是最不容忽视的因素。高达26.89%的丧偶率即意味着在60岁以上的老年人中,每4个人就有1人失去固定伴侣。
类似光叔、熊大爷这样的丧偶老人在我们的采访中并不少见。吴伯老伴去世多年,两年前也开始思考结婚共度晚年的计划。可老人的婚姻受制于金钱、子女,囿于对一段关系的重新适应,在事情尘埃落定之前,吴伯偶尔也会铤而走险。
伴侣因生理衰老或疾病导致的性功能丧失或性欲下降也是老年婚外性行为发生的推手之一。
妻子因病抗拒亲密接触,老何面临着夫妻需求落差的现实问题,但性生活于他是“非要不可的”。他看过性方面的书籍,了解到性压抑的危害。年轻时做建材生意攒的积蓄,让他有足够的底气去寻求新鲜事物,不至于囊中羞涩,这其中便包括平衡性需求的开销。
离开伴侣,女性性工作者是最隐蔽,也是最简单直接的释放途径。
老何苦闷,自觉没有伤害任何人,却得和贼一样行事。在他看来,性与爱无关,它仅仅是一种生理的需要,或者说,爱不是什么重要的东西,也并不存在,“像我们普通的凡人,一个普通老百姓,哪有什么爱情呢?”
与其说老何不懂爱,不如说在和伴侣几十年已成模式化的相处中,激情退却,原先对于对方的欲望早已转化成熟悉、如老何所言的“左手摸右手”的麻木的亲密感。
美国家庭治疗师 Esther Perel 认为,亲密和欲望是一对天生的敌人。67岁的陈香港隔几个月就会去一些洗浴中心“消磨时间”,与其说是生理发泄,他觉得这更像是一种“生活情趣”, “天天不就是上班,下班,吃饭,睡觉,老婆跟你聊来聊去都是那些东西,还是需要一些新鲜感。”
在家里,陈香港面对老婆不时的质疑查岗,每个礼拜的性生活变成了例行公事,“就当交功课喽。”
要说上面这些都还是偏向于生理方面的满足,那么对于古伯来说,“隐蔽的性”则是他补偿情感缺失的工具。
古伯的父母在他四五岁时离婚,父亲后又续了弦,他的童年时期一直是跟奶奶生活的。在25岁那年,古伯鼓起勇气对一个女同学告了白,不料反被公开了情书,他说,从那以后他“再也不相信女人了”。
古伯老婆早在多年前出轨,夫妇两人分床7年,终于熬到女儿高三毕业,早已破裂的婚姻在前不久宣告结束,他形容自己在家就是“吃软饭的”。
从前在工作岗位中得不到尊重,回家还要忍受老婆日日的冷嘲热讽。现在能离婚了,但窘迫的经济条件没有给他潇洒离去的机会,古伯还是得带着老父亲跟前 妻住在同一屋檐下,爸爸睡一间房,自己每晚则缩在客厅的沙发里。
“我是不信命的,我有时也认命,但是我不信命。”古伯时常跟我们感慨“命运不公”,但他对自己的理想伴侣还是有着完整的想象。
“这个心目中的人呐,你们不要笑我,我的梦想就是找一个高素质的,身高至少1米63以上,皮肤比较白, 性格要好一点⋯⋯”他顿了顿,“尤其是能够对我再关注一点儿, 我还是有这种愿望吧。”

“爱情这个东西都是可望不可即的。”古伯转头又推翻了自己,于是他从婚外性中寻找满足感, “因为性是可以用来交易的,爱就不能够。”
古伯恐惧衰老,面对街上潮涌而过的年轻人,他不住感慨“无可奈何花落去”,性却给了他“正在恢复年轻时未被充分调动和激活的潜在青春细胞”的美好感觉。
对古伯而言,这样的性体验里,没有人会计较他是否成功,被关注甚至被欣赏的渴望通通得到满足。他回想起曾经那些见不得光却美好的性经历,感觉自己就是动物世界里的“猴王”,“因为我有权威啊,还有能量。”
古伯的微信里加了大大小小几十个“老板交流群”,他坚信自己的股票分析系统终有一日会给他带来金钱,带来名望,带来真挚的感情,“我不是普通人呐,即使现在是,将来我不会只是一个普通人的。”
健康快乐每一天个人博客版权声明:以上内容作者已申请原创保护,未经允许不得转载,侵权必究!授权事宜、对本内容有异议或投诉,敬请联系网站管理员,我们将尽快回复您,谢谢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