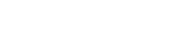刘晓春:全面理解“老龄化”

原标题:刘晓春:全面理解“老龄化”

刘晓春/文
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人们越来越关注将来养老资金的筹集、如何应对人口红利的消失、如何阻止人口总量下降等问题。然而,人类遇到的问题恐怕并不是这么简单,也不是那么悲观。就人口结构而言,人类或许正在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遭遇的是千万年不遇的大转折。
人类历史上各个区域、各个群落经历过无数的人口数量和结构的变化,大多数是因为自然灾害、瘟疫、气候变化、战争等因素造成的。其中尤其是战争,不仅造成人口数量的大幅度下降,也会带来人口中男女性别结构和年龄结构的剧烈变化。但随着这些特殊事件的结束,人口结构很快就会恢复我们认为的常态。马尔萨斯等认为,随着人类技术的进步,物质供应会更加丰富,但这增加的供应很快会被增加的人口所消耗,于是会出现灾害、瘟疫、战争等调节人口数量,同时人类自身也在不自觉地改变生育数量和频率,以应对环境的变化,从而调节人口的数量和结构。可以说,在前现代社会,人类人口结构虽然总是在变化中,人口总量随着物质供应的丰富不断增加,但总体上保持着人口结构的常态。
现在进入的“老龄化”社会,是在这样一系列背景下出现的:首先,人类科技快速发展有效解决了人类生存的物质供应约束,可以说,现在在总量上不存在物质供应不能满足人类生存的问题。现在还存在饥饿和贫困现象,是人类包括经济的、政治的社会制度造成的;其次,由于科技的进步,人类生育意外和婴幼儿死亡率大为降低;第三,因为营养充足,居住环境改善,医疗发达,人类意外死亡率也大为降低,寿命延长。所谓寿命延长,不仅是平均寿命这个数字,而是人们普遍的长寿。在前现代社会,长寿只是极少数人,绝大部分人类没有机会长寿。所以,只要人类的科技继续发展,人类就有能力保持普遍的长寿,除非发生毁灭性的气候灾害和战争,否则,在主要国家和区域,65岁以上人口占25-30%将会是常态,促进生育也不可能改变这个趋势。既然是常态,那么,在未来也就无所谓“老龄化”了。
因为人口结构这样的大转变,对人类生存和社会治理带来了一系列的新问题,而不仅仅是如何筹集养老资金这么一个问题。
一、养老是任何社会都面临的社会治理问题。不同社会阶段需要探索不同的解决方式。
席勒在《钓愚》一书中说,美国人没有量入为出和储蓄的习惯,退休后的赡养是一个很大的社会问题。政府最初希望通过教育和引导的方式,让人民养成量入为出和储蓄的习惯,但是没有用,于是有了社保系统。社保一定意义上起到了强制储蓄的作用。
孟子提倡“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礼记》更将“人不独亲其亲”、“老有所终”、“鳏寡孤独皆有所养”列为大同社会的必要条件或标志。“鳏、寡、独”也是老去的状态,并且是无法实现家庭赡养的状态。可以看出,那个时代“养老”,包括弱势人群的赡养就是突出的社会问题。孟子希望从道德层面倡导,《礼记》并没有提出制度性的方案,共同的是,养老不仅仅是钱的问题,还有如何养的问题,需要社会机制来解决。历史上,西方教会等组织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中国则是宗亲体系发挥力量一定的作用。但总体上,中国历史上还是“孝道”、养儿防老、量入为出、勤俭节约等文化观念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现代社会的老龄化问题与以往时代有很大的不同。首先是老龄人口所占比重庞大,如果不能很好的安置,肯定是一个重大的社会安定难题;其次是每个个体需要赡养的时间长度大大延长。以前社会一般可能需要赡养10年左右,现在起码是20年;第三是由于现代工业、服务业和城市化的发展,家庭单位越来越小,没有家庭赡养的环境;第四是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事业和生活方式。许多家庭成员都分散在不同的城市学习、工作、生活。中国人虽然依然注重孝道,但在这样的生活方式下,家庭养老难以为继。因为人的寿命延长,还出现了一个现象,当一个人退休进入被“养老”的行列,会赫然发现,他上面还有需要赡养的父辈,而对于他的下一代来说,则有两代老人需要赡养。如果再考虑独生子女因素,这个压力就更大了。
社会化养老,并且让每个人都能有尊严地老去,是现代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
二、理性看待“人口红利”,让人口结构在发展中自然平衡
经济,是一种人类社会现象,所以人是经济增长的绝对动力,年轻人更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关于老龄化社会,人口红利是讨论得比较多的一个概念。所谓“人口红利”是占比较高且庞大的、低收入年轻人口给经济增长带来的福利。有认为,中国过去40年的高速发展,主要得益于庞大的人口红利。应该说,过去几十年的高速发展有人口红利这个因素,但并不是绝对因素,占比较高的年轻劳动力人口并不必然带来“人口红利”。
如果因为年轻劳动力人口占比高就会有“人口红利”,就不能解释为什么改革开放前没有产生这样的人口红利,更不能解释在改革开放开始不久将“一孩”政策作为国策。同样不能解释目前世界上许多第三世界国家依然处于贫困之中。
单纯就人口红利的理论说,产生人口红利的重要前提是,大量农村过剩劳动力向非农业产业转移。没有这个转移过程,就只有农村过剩人口,而没有红利。一旦农村过剩劳动力转移结束,就来到了所谓“刘易斯拐点”,人口红利消失了。这是对人类经济现象观察所得到的一个结论,实际上与人口老龄化无关。那么,如果脱离农村过剩劳动力人口向非农业产业转移这个基本条件,就不应该再是这个理论的解释范围。或者说,刘易斯的这个人口红利理论不能解释人口老龄化。我国前40年的高速发展,正是改革开放带来了工业化、城市化、全球化过程,为农村过剩劳动人口提供了充分的就业岗位。就这个角度说,刘易斯理论是有一定的解释能力的。
没有农村过剩劳动力人口向非农业产业转移,在其他状态下,就没有刘易斯定义下的“人口红利”,但人类的经济也还是需要增长的。就我国现阶段而言,需要进一步改革开放,需要进一步推进城市化,需要进一步推动科技创新和科技产业化,需要进一步激活市场和提高要素配置效率,需要进一步推进现代农业发展,需要推进共同富裕以扩大内需。即使是刘易斯理论下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业产业转移,其重要前提还是市场化条件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大发展。没有这样的前提条件,农村剩余劳动力人口不仅不会产生“人口红利”,反而会成为历史上的流民,社会动荡的源头。
人口的年龄结构有没有可能回到以前的状态?几乎是不可能的。即使有自然灾害、流行瘟疫、大规模战争的影响,就人类已有的科技能力、医疗卫生水平,人类依然会进入绝大部分人健康长寿的状态,60岁以上人口占相当高的比重。在前现代社会,人类在任何年龄段都因为营养不良、疾病、暴力及意外等原因有相当高的死亡率,许多人根本没有机会老去,更有不少比例的人口没有机会成年。
有没有可能通过提高生育率来提高年轻人的占比?理论上是可能的,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前现代社会有非常高的生育率,但因为所有年龄段的死亡率高,造成进入老年阶段的人口相对很少。现代社会由于绝大部分人类都能进入老年阶段,通过提高出生率以确保老龄人口保持一个比较小的占比,但更多的婴儿未来都会老去,意味着老龄人口的绝对量会越来越庞大,同样也意味着未来需要更高的出生率来确保老龄人口占比的稳定。这样的趋势,可以说是灾难性的,以这样的策略来阻止人类进入老龄化社会,也是愚蠢的。人类即使现在殖民火星,火星很快也会承受不起的。
人类社会应该与地球上的其他生物一样,在物种数量上有一种自然的自我调节机制。前现代社会生育率之所以高,并不是因为经济条件好、生活条件好,恰恰是因为要对冲各个年龄段死亡率高的风险。斯密在《国富论》写到他的观察,穷人生孩子的数量往往多于富人。这背后的原因,可能就是穷人由于生活困难,孩子的存活率低,而富人的孩子有充分的营养,有获得医疗的能力,存活率相对比较高。现代社会,城市生活、妇女走出家门等或许是生育率降低的显性经济原因。
三、重新划分人类的年龄段,重新安放不同年龄段人类的身心。
《礼记》关于大同社会的描述短短的107个字,很平淡,没有什么太过深奥的、难以企及的高标准道德要求,但仔细分析,几乎每一条都不容易做到,或者说人类历史就没有解决过这些问题。其中关于不同年龄、不同状态人的安置就有42个字,占了近40%。“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可见,每个人在社会中得到适当的安置,是任何社会面对的重大问题。“安身立命”,是每个人的头等大事,人所有的努力与奋斗,都是为了“身”“心”获得一个合适的寄托与安排。在人生的不同阶段,其“身”“心”所安的要求是不同的。“安身立命”,不仅需要个人的努力,也需要社会提供适当的空间。
这些年,“中国大爷”、“中国大妈”成了新的流行词。中国大爷们背着单反满世界寻找美景;中国大妈们披着丝巾周游各国摆POSS。广场舞,不再是大城市的现象,而是遍及大小城镇的景观。
如果说,以前60岁以上人群的年龄结构是一个陡峭的圆锥形,现在则是一个胖胖的秤砣型。60-80岁与40-60岁,是差不多庞大的群体。这其中60-75岁人群,大多数身体健康,思想活跃,与以前这个年龄层次的老态龙钟完全不同,正是他们组成了中国大爷、中国大妈的靓丽风景。他们退休之时,既感到兴奋与幸福,又感到震惊与迷茫。因为终于可以轻松潇洒过自己想过的生活而兴奋,都有信心活过90岁而感到幸福;但他们也突然震惊地发现,退休以后居然还有30多年的日子,几乎和工作的时间差不多长,不知道该如何度过这漫长的日子。可以说,现在与今后,60-75岁这个人群与75岁以上或者80岁以上人群是完全不同的两个群落。所以,有必要对人类不同年龄段进行重新划分,但不是简单地把某个阶段的年龄拉长,比如把青年的年龄上限划到50岁或更高,而是需要增加分类。比如在传统的婴幼儿、少年、青年、中年、老年中间,再增加一个档次,把65岁到80岁称为“年轻老人”或“壮年”。“年轻老人”是客观描述,也有双向的心理暗示,“壮年”也是客观描述,身体依然强壮,壮怀依然激烈,当然更是鼓励。既然有了这个类别,就需要有相应的安置。
现在有提出提高法定退休年龄的建议,还有建议鼓励退休人员再就业。这些都需要考虑。但这同样会带来很大的社会问题。首先,由于年轻老人的总量与中年人、青年人的总量相差不大,退休年龄提高,中年人、青年人上升通道将会被严重堵塞,严重影响企业、机构和社会活力,这会成为企业、机构乃至社会的治理困境。其次,由于数字技术的快速迭代,创新层出不穷,许多企业不仅只招聘35岁以下人员,甚至不断在淘汰35岁以上员工。延长退休年龄,无疑会增加这方面的就业压力。第三,如果开设专招年轻老人的企业,作为特例或许可以,考虑到企业的活力,恐怕很难成为主流模式。
年轻老人的身心安处,是一个全新的社会治理问题。解决这个人群的安置问题,需要政府引导与市场发现。提高法定退休年龄不必操之过急,而是可以考虑退休人员创业或再就业。“银发经济”不应该只是关注老年人的消费,还应该包括老年人口创造价值的一面。一方面,工作了三十多年,人的身心确实需要调整一下。先退休,调适一下身心,再选择适合自己的,或自己喜欢的工作,创业或就业,可以重新焕发青春,更可以为社会创造价值。另一方面,由于有这个群体的存在,政策又有鼓励,市场一定会为这个人群找到发展空间。农村过剩劳动人口转移到非农业产业能够产生“人口红利”,那么通过适当的政策鼓励,打开市场,这个既有相当消费能力,又有创造欲望的群体也可以产生新型的“人口红利”。
政策上可以考虑:1、允许并鼓励退休人员再就业或创业;2、退休人员再就业或创业期间,照样享受社保待遇;3、退休人员再就业、创业的工资收入免税;4、退休人员创业,根据不同企业类型给予税收优惠;5、退休人员创业,投资款退还已缴纳的所得税;6、企业招聘退休人员再就业,可以参照福利企业的方式给予一些优惠政策待遇。当这个人群的安置常态化后,可以考虑调整甚至取消这些政策。
当年轻老人寻找“我心安处”的时候,真正的耄耋老人遇到的是如何老去难题。以现在人类的生活方式,以及未来的趋势,家庭养老肯定不是最佳的选项。首先,从有利于老人身心考虑,康养机构不应该设在交通不便的城郊僻壤,那里虽然空气新鲜,但人气沉闷,老人并不喜欢每天看到的都是暮气沉沉的人们,他们需要亲人的关怀,也需要看到年轻的世界。所以,康养机构应该设在交通方便的城市中心地带,最好是在学校、幼儿园旁边,孩子课间的喧闹正是对他们心的安抚。其次,金融领域,除了提供养老资金上的服务,还要增加养老方式上的服务。比如养老信托、家族信托业务中,增加养老监护信托的服务内容。一般社会会为无人照顾的小孩指定监护人,却没有考虑为在养老院无自理能力的老人指定监护人,金融信托机构可以作为这样的监护人,即受委托对在康养机构养老的老人进行监护,监督养老机构的服务质量,确保受信托的老人被尊严地对待。信托机构可以聘用年轻老人担任监护巡视员,定期或不定期到养老院巡视,并代表老人的监护人与养老院方面进行交涉。这个工作或许是适合年轻老人的。
2022年10月28日星期五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责任编辑:
健康快乐每一天个人博客版权声明:以上内容作者已申请原创保护,未经允许不得转载,侵权必究!授权事宜、对本内容有异议或投诉,敬请联系网站管理员,我们将尽快回复您,谢谢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