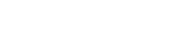艾滋病老人,被欲望击垮的晚年

本文授权转载自“真实故事计划”
作者:秦月
我是一名护士,在成都一所公立医院的消化内科。正常来说,我们只需要处理一些常规疾病,病人来自周围小区,交上一千块钱的门槛费,住一个星期就可以出院。
四川省内凉山地带,一直是缅甸云南向内地运毒的必经路线,相比于一般的城市来说,作为四川省省会的成都,艾滋病患者更多,我们科室也偶尔会遇到病患。
遇到的第一个艾滋病人是个普通的个体户老板,三十多岁,打扮体面。一开始只是因为吃不下饭来看医生,但是一项项检查做完都没问题,最后发现是HIV 阳性。
医生把他请到办公室去谈话,进门之前兴高采烈和病友聊天,出来就像换了一个人。

剧照| 最爱
相比于这种被突然发现的情况,艾滋病在老年人里蔓延的速度更让我惊讶。2017年,老年人首次被国家列为艾滋病防控的重点人群。不过,和年轻人输血、吸毒、高危性行为多种传播途径不一样的是,老年人的患病途径异常单一。
这其中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位叫车庆林的老人。
二
14年春天,很平常的一天。我在住院部,刚升为护理组长,管理十二张病床。这天急救车送来了一个晕厥病人。
他就是车庆林,年龄62岁,头发白了一半,长期从事体力劳动使得他脸色黝黑,看起来像七十多岁的老人。他安静躺在病床上,我给他量血压,他伸出手,手指蜷缩如鸡爪。
介绍完病区环境和主管医生,我请他在知情同意书上签字。他有些不知所措,我又解释了一遍,把笔递给他。“哎哟,我好多年没写过字了。”接过笔,他有些不好意思,以一种别扭的姿势用力攥笔,一笔一划在签字栏上写下自己的名字,字迹很重。
我告诉他,住院病人要留家属联系方式,他踌躇半晌,写下歪歪扭扭的车庆松三字,关系一栏他写下“哥哥”。我和他说关系不能写哥哥,要写“兄弟”。
“老师,给你添麻烦了。”我给他重新拿了张签字单,他这次正确填完了。
“还有电话。”我指着联系方式一栏提醒道。“我不记得,要看看。”他从外套里掏出一只老式诺基亚基础款手机,一个一个翻出电话号码看,入院介绍和签字花了半个小时才完成。
输液的时候为了缓解他的紧张,也为了增加彼此之间的信任,我一边操作,一边和他聊天。
他是位农民工,曾经有过一段婚姻,还有一个儿子。但是由于夫妻感情不和,两人早早就离了婚,之后的这些年也没有再婚。
“你儿子多大了?”我好奇地问道,心里纳闷他为什么联系家属没有留儿子。
“二十八了。”
“做什么工作哟?”我笑着问。
“成都的银行上班。”他嘴唇紧闭,抬头专注看起电视,可能和儿子的关系不大好。
三
车庆林的体重在三个月之内下降了十二斤。
一开始,由于他的血液分析结果,主治医生怀疑他是白血病。住了一个多星期,症状却没有减轻,脸色发黑,嘴巴发白起皮,肋骨根根突起。
医生给他做了两次骨髓穿刺,一寸多长的钢针打入他的髋骨,粘稠的淡粉色骨髓被抽出。他疼得咬牙切齿,却能坚持不动。
两次结果出来,没有明显异常,大家想起了另一种会引起发热和白细胞增高的疾病,化验结果很快就出来了,HIV抗体阳性。

剧照| 最爱
车庆林得的不是白血病,是艾滋病。在下午安静的走廊里,我扶着他去办公室。知道结果的时候,他张大嘴巴,露出几颗黄黑的牙齿,保持这个姿势好几秒。我们以为他不知道什么叫艾滋病,正准备向他解释,他却动了,脸上似哭似笑,轻轻叹了句:“咋是这个病?”
我们心里也是崩溃的。他在科室内住了大半个月,大半的医护人员都接触过他的血液。科室里一片死寂,护士长拿来了职业暴露表格单,我们围着长长的办公桌,写下自己的名字。
在医院,这样的事情是不可避免的,一次又一次的担惊受怕后,我的心早就麻木了。大多医护人员都是及时行乐的享乐主义者,因为明天真是太飘渺了。填完表格,每个人抽了一管血送去化验,然后继续工作。
等到他消化了一天,我们委婉建议他转院接受专业治疗。他听了我们的建议,摇了摇头:“还是算了吧,就住这里,不折腾了。”传染病医院在市中心,是一家很有名气的三甲医院,各种费用都比这边高出三分之一。虽说艾滋病国家有补助,可是那只是艾滋病的药品费用,用药检查都需要他自己掏钱。另外一个问题是,市中心离他家有三十多公里,带东西、家属照料都不方便。
“还是你们这儿的老师和气,我信你们。”他轻笑着说道,眼神中却有说不清的东西,我不敢看。大家知道,他再信任我们,这个病也没法治好。
我们只能把他转进单人病房,每天进行空气消毒和地面消毒,垃圾专门放置。
四
自从知道自己患上艾滋病,车庆林变得沉默起来,不是在睡觉就是发呆,电视不看了,病房不出了,安静得可怕。
考虑到他的情绪,在不涉及血液和体液接触的情况下,我和医生尽量不戴手套与他肢体接触。慢慢地,他开始愿意回答我一两句话,但一问到染病的途径,他就把脸扭过去对着墙。
可我们要上报,没有办法,只能通知家属。车庆林的哥哥、弟弟和老母亲围在病床周围,老太太哭成泪人,两个兄弟连病床都不想靠近。我们让车庆松和他交谈之后,他才承认由于单身多年,和一些失足妇女有长期的不洁性生活史。
“我这是活该啊?”他低垂着脑袋,看不清表情。
“你不要这么说。”
“你为啥子不再婚?”医生合上病历问他。
“没得钱,有哪个女人愿意跟着我。”他自嘲一笑,“离婚后,我的生意就赔了本,去外面打零工,工地上爬滚,女人看都不看我一眼。谈过一个,是个离了婚带孩子的,在工地上烧饭,只好了一年就散了,天天就是找我要钱,根本不想和我正经过日子。”
“你怎么不用安全套呢?”医生叹口气,“社区有免费发放的。”
“羞都羞死了!人家要戳断脊梁骨的!”他摇摇头,“我哪敢去拿?这样的新鲜玩意儿,拿了我也不会用。”
他又加了句,“她们也没说要用。谁晓得会得这个病?那不是外国人得的吗?”
五
车庆林嘴里的“她们”是一群徘徊在工地附近的妇女,我也见过一次。
有次我和同事出诊回医院,路过一片偏僻的工地。一个大姐过来敲车窗户,我在后座睡觉,听她殷勤地邀请开车的男同事下去玩玩。
那些妇女年纪不小,从三十多到四五十岁不等,专找些单身汉做生意,看见车就拦,一次只要二三十。
抛弃掉生活的希望后,性的获得变得简单,快捷又经济。
“他没文化,什么都不懂。”站在走廊尽头,车庆松一脸嫌恶,“这真是丢人!老车家的脸都丢尽了,他不光害了自己,还要害大家。”他望着我们,一脸无奈。

剧照| 最爱
“还不如得白血病,那个至少不传染。”弟弟皱紧眉头。
医生建议家属把车庆林接回家,度过最后阶段。“那不行。”车庆松大叫道,“他这个病,不能回家,就在医院里。”我注意到,车庆林的嫂子弟妹和姐妹都没有来。
“对,回去怎么行?”弟弟也连忙摆手。
我说他现在的情况必须需要一个看护,没有家属留陪,绝对不行。车庆松犹豫了半晌,说他一定想办法。老母亲一直站在边上抹眼泪,说完话,他们逃跑一样地拉着老母亲匆匆而去。
六
车庆林再也没能离开医院。
住到一个月的时候,他的病情开始急剧恶化。先是发高烧,每次体温都在41°以上,酒精擦浴、退烧针都没有效果。高温一直持续,他的脸像一块烧红的炭,看起来三分像人七分像鬼,实习生和新来的护士都不敢进他的病房。
好不容易退烧了,他的身体开始脱皮,红彤彤的胳膊看起来十分诡异。打针时,压脉带一系,整条胳膊就变紫;压脉带一松,皮肤就裂开,血液顺着手臂流下。血管变脆了,一个新扎的留置针,用了不到一天,再次输液时,皮下渗出一个大包。
有次他正和我说着话,突然开始剧烈咳嗽,好几分钟后,他才缓下来,松开捂着嘴的手,我看见手心里都是血。
“秦老师,我怕是不行了。谢谢你们,现在也就你们不嫌弃我了。”他说。对我们,他一直怀有很强烈的负罪感。平时有眼生的护士来量体温,他都要向特别说明:“我是艾滋病,你们要小心。”电子体温计,根本不会接触皮肤。
然而他清醒的时间越来越少,开始神志恍惚,一瓶液体还没输完,手上的针就被扯落。
艾滋病晚期,需要专人照看,医院连个上特护的人员都抽不出,只好再次联系他的家属。
医生给他的兄弟打遍了电话,家属们不愿意来医院照看病人。请护理员,他们的条件差,出不起钱,这个病给钱估计也没人来,最后家属告诉了我们车庆林儿子电话。
电话打通了,来的却是个黑胖妇女。
七
“我是他从前那个。”她的嗓门很大,穿着一身花花绿绿的涤纶衣服,一张脸圆乎乎的,看不出年龄。这是他的前妻。
她有着川渝地区特有的干脆泼辣,我把手套口罩给她后,她收起来,坐在床边的椅子上,一边看着吊瓶一边绣十字绣,两米长的孔雀牡丹,上面密密麻麻爬满五彩绣线。
车庆林扭动手臂的时候,她套上手套,胖乎乎的大手按住他胳膊肘。“莫要板!你都这样了,莫要再害人了。”她来了后,车庆林虽然还是神志不清,却没有之前的狂躁了。

剧照| 最爱
我问她怎么愿意接下这档子差事。她苦笑:“莫得办法呀。他们都不来,喊我儿来,我儿今年婚都还没有结,我替我儿来,我个老太婆,我不怕死。”
“他就是害人。以前年轻挣了钱,在外面找女人,把钱给外人花,不然我们也不会离婚。”她朝昏睡的车庆林努努嘴,“老了,还是死在女人身上了。”
她离婚自己带着孩子,开一家小饭馆,后面又嫁了个老实人,一人养家,供儿子上大学,没要车庆林一分钱。
她嘴里骂,心肠还是软。车庆林大小便失禁,床上得铺一次性床单,上面再铺护理垫,臭气冲天,她力气大,一把将病人翻身,动作极快的擦洗,一人能顶两个护工。
车庆林的儿子在休息时也会过来,高高胖胖一个年轻人,穿着白衬衣深色西裤,看起文质彬彬,一点也不像车庆林,他像母亲更多些。他总是坐在医生办公室,听医生一边写病历一边说。他的话很少,提起父亲来低着头,声音很轻。他在病房的时间也不多,通常是看一会儿父亲,和母亲说几句话后安静离开。
车庆林早就不认识人了,对着儿子也说不出话。但他还记得前妻,她喂饭,他会听话张开口;她和他说话,他会哼哼回应两句。我用电筒照他的瞳孔,指着人问他:“车庆林,这是谁?”
“这是我老婆。”他的脸上带着一抹笑,完全忘了他们已经离婚多年的事实。胖妇人站在一边,仰着头望着窗外,使劲眨巴眼睛。
住满两个月的时候,他开始长时间昏迷,医生建议让他回家。这边农村的风俗,病人在自己家里咽下最后一口气比较好。家属们却纷纷摆手,依旧不同意。
车庆林咽气不久,抬尸人就赶了过来,一个黄黑相间的PU袋子包裹住他,两个工人轻松扛起他。
他的家属们走得匆忙,既没有在病区烧黄纸,也没有在楼下放鞭炮,无声无息地就奔向了火葬场。
作者秦月,护士
健康快乐每一天个人博客版权声明:以上内容作者已申请原创保护,未经允许不得转载,侵权必究!授权事宜、对本内容有异议或投诉,敬请联系网站管理员,我们将尽快回复您,谢谢合作!